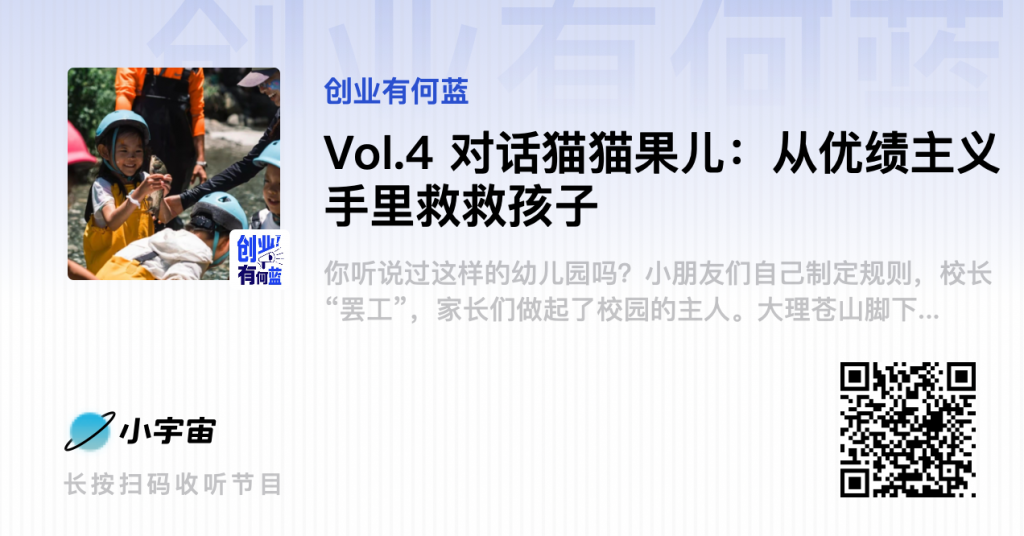你听说过这样的幼儿园吗?校长“罢工”,小朋友们自己制定规则,做起了校园的主人。大理苍山脚下就有这么一家名叫猫猫果儿的幼儿园;十二年前,办了十年支教学院的陈钢,为了躲避雾霾带着孩子来到大理,开启了自己的幼儿教育实验。
陈钢相信,比起被管教,孩子更需要自由。在猫猫果儿,孩子们被鼓励去观察、质疑、制定规则;而在孩子、家长和学校之间,陈钢试图用社区生态来取代传统的“教育购买”模式,三方共创这所学校——这大概算得上DAO在教育上的早期实践。
一个人全部的秘密都藏在童年。如果真是这样,给孩子创造快乐的童年对于社会的正向发展至关重要。很多人即使成年,内心依然背负着童年留下的伤口,限制自己,也伤害他人和社会。而AI时代的到来,又给教育带来了新的变量:我们如何帮助孩子去构建内在的牵引力?如何引导他们把生命玩成终身成长的无限“游戏”?
对教育的探索和科技投资一样,都是试图构建更美好的明日世界。在2025年的开端,我们先来关注明日世界的主人——孩子们。本期播客我们邀请到了猫猫果儿的校长陈钢,聊聊如何教育出快乐小孩,AI又会怎样帮助我们,enjo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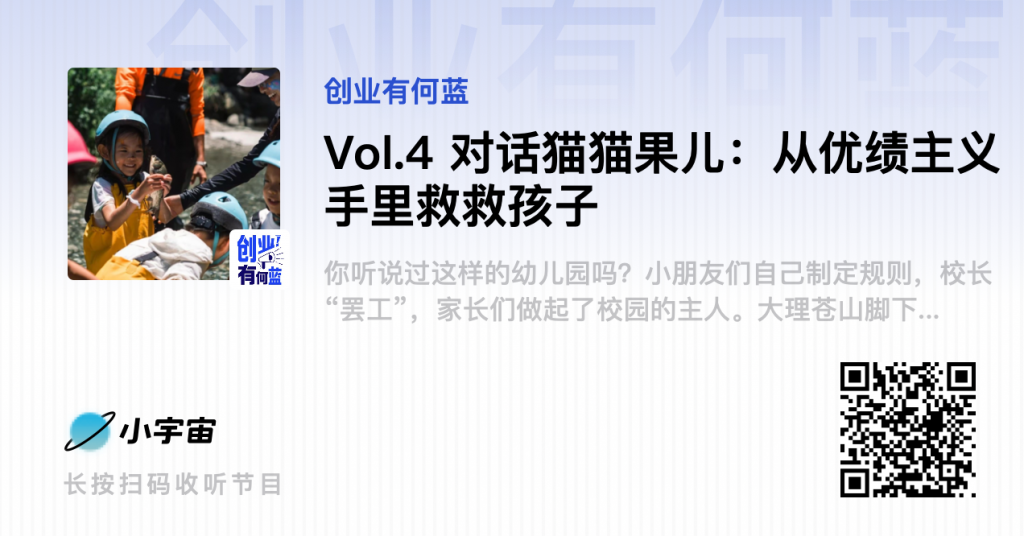
以下为对话全文,有删减和编辑:
朱天宇:2013 年9月份,我偶然探访了大理的猫猫果儿幼儿园。原本的出游变成了一个大理教育探寻之旅,那时我才意识到大理是一个教育创新的肥沃之地,多么有意思、有理想的人在这里寻找教育的可能性。我想今天的问题就从这个经历开始:为什么开始投身做这类教育?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哪些重要的选择?
陈钢:2007、2008年那会儿北京沙尘暴特别厉害,北方和上海有很多家庭移居到大理,通常是中产阶级或知识分子家庭。其实雾霾问题主要是孩子的问题——担心孩子的身体健康,所以来到大理的这群人也很看重孩子的教育。当年大理有十几、二十个家庭联盟,就是几家人凑在一起办个幼儿园,自己教自己的孩子。听上去很好,但是孩子之间发生了纠纷、教育理念出现了分歧该怎么办?往往就是死磕、散伙。当时我意识到,这些创办者的教育理念是非常受限于自己的原生家庭以及亲子关系的,不是好的幼儿教育。所以2008年开始我和太太就到全国各地学习幼儿教育,2012年左右,我们做了第一个幼儿园,就是猫猫果儿。
朱天宇:我觉得在讨论猫猫果儿之前有个问题得先明确:你到各处去学习是想探究什么是好的教育,那你看到当下教育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陈钢:首先是原有的选拔制度所配套的人才标准在当下已经失效了,未来需要的并不是能和流水线、制度完美匹配的人,而是能创造出更多可能性和更高级欲望的“活人”。这是对未来人类非常重要的命题。第二点是“人如何自处?”比如在猫猫果儿毕业的孩子,会天然认同两件事:世界上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我认为我很好。这就意味着孩子们是以自我评价为主,而不依赖外部评价激励。外部评价可以推动孩子走向复杂和丰富,但是强大的自我认同是Ta对世界抱有希望的来源。很多孩子可能直到长大都不能完成这样的自我认同。
朱天宇:所以你找到的解法是什么?
陈钢:我们的教学研究有一个现象到理论的闭环,发现现象、展开研讨、闭环成理论,这样幼儿园差不多用了两到三年时间形成了教育系统。概括来讲,在幼儿园中我们教的是心智模型,也就是人是怎么长大的,人在面对多元、他人、自由或者规则的时候会有什么样反应,让孩子从底层慢慢建立起认知。
我们的幼儿社区有三个维度的课堂:幼儿园、教师学院,家长课堂。所有人参加课堂有一个前提条件:自愿参加。什么叫社区?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这样就构成了这个幼儿园的底色——自由。
朱天宇:一个关键词出现了:自由。
陈钢: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我们第一个写到纸上的规则是怎么来的呢?四个孩子在沙坑里面玩,一个孩子不小心把另一个孩子的堆沙作品踩了,两个孩子有了冲突。老师就问孩子:现在我们出现矛盾了,怎么处理呢?有个孩子说:我们要开会。因为幼儿园里每天早晚都要开一个会,孩子们会回顾:昨天晚上放学后发生了什么?今天我过得是开心还是不开心?这样进行一段时间后,他们就学会了开会。
那天开会他们定了一个规则:如果在沙坑里做了作品,小朋友需要在作品旁边插个小树棍,代表作品需要保留。
老师又问:你们认为规则是什么?小朋友讲:规则是为了让大家都开心。
那什么时候要定规则呢?当我们发现有一个人不开心,而且他的不开心会影响到我们的时候。(笑)
我觉得这是两个非常探底的问题,定这条规则的孩子平均年龄只有四岁半。过去十年猫猫果儿所有的规则都是这样制定出来的。

猫猫果儿同学笑笑的自画像
朱天宇:过去十多年我跟陈钢持续地在交流,我发现了猫猫果儿最重要的特点:它不是在构建一个学校,而是在构建一个社区/社群,学生、家长、老师,所有的stakeholder(利益相关者)共同建造了这个社区。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在无形当中完成了教育的三个支柱: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所以我想再追问:社区怎样去发挥教育的功能?
陈钢:这里面是有很强的专业性的。我们的理论基础是建构主义,首先得发现问题、锁定问题,模型化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之后再用匹配这个问题的方式去设计教案来解决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问题的底层是什么,同时要明白当下的问题只属于这个时代——20年前也许当下的问题并不被视为问题,反而是一件好事。因此当这个时代的新问题被我们看见了,你只能用这个时代的方法去解决。外部经常觉得我们在创新,但其实我们是在不停发现问题。
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很困扰,因为每一个家长都有绝对的话语权,他们都希望把这个学校改造成他们理想的样子,所以父母和父母之间就开始吵架。这时候我就「小事化大」,激发各种讨论,让父母们吵得不可开交(笑),迫使他们也成为了教育研究者。这其实也把幼儿园的课程思路转移到了家长社区。
朱天宇:对,我记得2016年左右,当时我去大理找你,你说你很烦。
陈钢:非常烦(笑),家长什么事都来找我。
朱天宇:那天你跟我探讨说要退出这个学校,让家长自己去解决问题,自己去建立规则,进行共治。后来你真的选择退了一段时间,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呢?
陈钢:这个很有趣。在学校最开始建立的时候,所有的教学都是自主的,老师想教什么就教什么。但谁来纠偏呢?是其他的老师和这个学校的拥有者——家长。我们会发现它进行了生态化纠偏——当这个老师的行为是对的,教研组会支持Ta,Ta的同事以及家长会给他很多正反馈;但是当Ta的同事关系出问题了,教研无法闭环,更重要的是家长看Ta的眼光、跟Ta聊天的口气变了的时候,Ta就知道出现问题了。因为在社区中,老师和家长的关系更像邻居。当整个外部环境对你都形成了排斥或者质疑的时候,这个老师一定会改变,家长也会改变,我们会发现这比任何评价系统都有效。
后来我们发明一个词叫“生态化评价系统”,就是用一个生态来给你反馈。从教育的角度上来讲,当你产生了强烈的自我认同,同时你是一个成长者的时候,环境给你的所有的反馈都可能会让你不够自洽。而你在寻求自我新的认知的过程中,真正的学习自然发生了。
朱天宇:挺有意思,就是去中心化导致大家不得不重视关系的构建,有了关系才可能形成你说的生态化评价体系。同时它也消解了家长认为自己在购买教师服务的理念,消解了这种有些对立的关系。
陈钢:刚开始顺利得不真实,每个人都非常亢奋,彼此相见都是笑脸。但当教学变得非常有序了,就会出现问题。这时候家长都特别渴望一个校长——也就是权威出来解决问题。这时候我有两个选择,如果我追求效率,那直接插手是最好的;但是我要做一件关于教育土壤改良的事情,我不做权威是最好的。后来我就跟家长开了个会,说我从此以后再也不进校园。直到今天我再没进过校园。
朱天宇:那大家可能会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你怎么评价自己的教育实践?标准是什么?
陈钢:我们开始的时候讲帮孩子形成多元世界观之下的自我认同,这是幼儿园的目标。
当年我犯了个错误,想在小学追求建构主义教育,帮孩子形成终身学习的能力。但当我们实践了两三年,会发现在小学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能力的结构化通常最早发生在初二到初三,那是人的学习模型真正落地的时候。小学阶段应该形成的是终身学习的动力,孩子的好奇心、他对世界的态度是能支持Ta未来终身学习的就够了,初中或者高中阶段的目标是找到热爱,根据热爱来结构化原有的知识库,才能落定学生的思维和心智模式。
那家庭教育呢,如果家庭的观念不能支持孩子的成长,学校教育做到 100 分都是没有用的。首先一定要让孩子处于复杂环境中。如果家庭给孩子创造了单纯的环境,再对都是不对。家长最负责任的是把孩子放在复杂的环境里,然后用爱来支持孩子。复杂环境不是说规模的大小,而是自由程度的高低。十几个自由的孩子能创造的多元性,远胜过几千个不自由的孩子。
第二,当孩子自由了,感受到各种新鲜的刺激,家长怎么引导孩子?有些家长会说:你别跟那个孩子来往;我来给你出头。我觉得都不对,家长需要给孩子一种感觉,叫做这个世界是可以被理解的,只不过现在我还不够了解。
其实只要家长和老师在不断成长,孩子成长是自然后果,力气不需要用到孩子身上。

猫猫果儿同学在魔法学院美术课上画的猫
朱天宇:你提到「找到热爱」,怎么帮孩子找到热爱?今天大量的成年人可能至今都没找到自己的热爱。
陈钢:一定是在社区环境中,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他人找到属于天命热爱。孩子面临的第一个环境是家庭,从Ta来到这个世界,父母对于Ta的好奇一直伴随着Ta主要成长阶段,极为关键的是,每当失控出现父母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好奇还是控制?如果Ta接受到的父母的眼光是好奇,那Ta大概率会找到天赋和热爱。如果父母的反应是规范、控制,那么很有可能会丧失。
在青春期里,由于伙伴关系中孩子有动机和对角色的追求,可能也会产生一种功能性热爱,但这不是天命的热爱。比如说,现在我在一个有八个犯人的牢房里,我发现我的智力是最好的,我总能够帮助老大实现他的管理目标。于是长此以往,我沉浸在连续收到正反馈的过程中,我误以为这就是我的人生价值。在这个例子中,人是被正反馈牵引得出的「热爱」,并不是由自己的追求得出来的。
如果说在整个小学或者是五年级之前,父母都是用好奇的眼光去看这个孩子,那么到了青春期这个孩子他会用自我领导力去进行伙伴协作,他就不太会因为伙伴的特殊性而丧失自己原生的热爱。
青春期的孩子可以模糊地找到热爱的方向,而从模糊到精准需要一生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主体是很难自评的,有时很难准确地说这就是我的热爱,但是我们从他者的角度来看也许会更清晰。我们提到要提供多元的环境,是因为在复杂的环境中,跟他人形成关系,探索才能更加完整。
现在很多人想要尽量减少和他人的复杂关系,这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我想可能是因为无论是工作关系还是家庭关系,总是不清晰、或者过界,大家担心受到压力。所有的关系都是交集,但是我们的文化、这个时代有一种力量可以覆盖所有关系。有时为了抗拒关系被覆盖,我们选择了不建立关系。这是一种矫枉过正,因为在一个复杂的环境里,我们才有能力或者机会去调节这个交集是什么、有多少。
朱天宇:一种更简单的理解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接触形形色色的人,而且必须要学着和这些人相处好,这个过程中一个人的自我觉识才会有提升,改善、驾驭关系的能力才能提升。不止教育,任何关系都是这样。沿着这个理解我还要追问你说的另一句话:「这个世界是可以被理解的,只不过现在我还不够了解」,怎么讲?
陈钢:这是我们给家长和教师的培训,当孩子接受到了外界的各种刺激以后,你应当如何引导孩子应对这些刺激?我想一定是用爱的方式去理解它,绝不是零和博弈和追求绝对公平。幼儿园和小学阶段,家长和老师非常容易当法官,裁决公平。这样孩子很有可能会在一个封闭系统内把自己长得非常结实,但是Ta会错过生命中的很多未知和可能性。零和博弈不具有共创能力,不具有发现的眼光,它的天花板是有限且单一的。
我们有过一个实验,收集了800多条临终遗言,发现可以分成五类。第一类是个人层的「隔壁老王欠我2万元,帮我要回来」,第二类是亲密关系层的「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你们娘俩」,第三类是社会层的「要不是小人背后捅刀我早就当大官了」,第四类是李叔同式的,临终时写下「悲欣交集」的人生体悟。你会发现,人只能向下而不能向上理解,这四类人所拥的自由程度完全不一样。其实我们的社会中大量的人停在第二层,我们可能无法理解「悲欣交集」,也无法理解马斯克追求时间和空间的自由。这个让我们坚定了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使人拥有更大维度上的自由。
朱天宇:你刚才说的对复杂性的认知、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是为了这个。
陈钢:为了让孩子穿透家庭给Ta创造的小宇宙,拥有更大的宇宙。我想这是可以通过社区化教育做到的。
朱天宇:AI 时代来临了之后,教育会面临什么新的挑战?你的一系列的目标、做法和评价体系会发生什么变化吗?以及怎样去应对?
陈钢:我认为重点会有偏移,现在看来AI对于教育的原理认知并没有很大冲击,但是它产生了更多的可能性。
小学阶段可以做的很明确:第一点是在开放的组织里快速形成任务型的小组,让孩子能够跟不同组员快速形成协作。我们在小学阶段希望培养孩子认知问题的能力,那么每研究一个问题都要给孩子找到最匹配的学伴,通过自我领导力和伙伴引导力来完成这个学习。
第二点是连续追问。面对问题,孩子向深探究直到能力穷尽,我们会发现这是个连续追问、能力建构的过程。每次探底孩子都得到了新的认知,Ta要不断把这个认知去迁移、应用到新的新的现象中。连续追问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苏格拉底式的持续追问,可以培养出具有建设性的批判者。还有一种是跟随好奇心的追问,我们会发现在小组教学中,好奇心会在讨论中被不断放大,你的好奇会激发我的好奇,可能还会激发更多人的好奇。这个过程有点像荒原漫步,我们是在好奇心的驱动下探究未知。
第二个维度叫做审美能力,当下它更加重要。在我们对未来的预判中, AI 可以快速地识别和满足你的欲望,这会导致满足的过程变得非常廉价。原来我们有大量的好奇和欲望,想要亲身参与和体验生命,似乎有无限的可能值得我们探索。但是当 AI 出现后,AI让很多原来被认为无限的事情突然变得有限了。这样的话你的生命价值到底是什么?怎么把有限游戏玩成无限游戏?怎样产生新的需求和欲望?我觉得这需要靠审美力来支持。
朱天宇:也就是说在以前,人的自我动机可能是被一些复杂问题牵引的。但是如果问题都被 AI 解决了,我们的牵引力从何而来?如何去构建新的牵引力?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AI 带来的挑战。那么如何用审美的方式解决呢?
陈钢:我觉得审美不是头脑决定的,也不是功能决定的,它是由感受决定的。当美来临的那一刻,时间是放慢的,头脑是消失的,判断力是没有的,所以美是一种感受。
朱天宇:你说的让我想起李安的一个采访,李安说电影一切的一切,最终的核心是创造一个moment。这个moment其实就是感受。而这是永无止境的。
陈钢:第一步是表达感受,第二步是能够在没有情绪状态的情况下把观点和事实列出来,第三步是找到与事实无关的观点和感受的关联,第四步改写感受才是目标。所以我觉得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是如此。比如我们刚才讲到面对新鲜的外界刺激,孩子不能继续自洽,感受并不好,但这恰恰是学习的过程,这个不好的感受是具有建设性的。